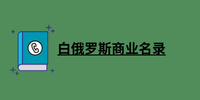我们不必研究所有相关规则,只需简要考虑一下区分原则,因为这是高等法院认为具有一定犯罪意图要求的规则之一(见上文)。关于该原则对个人的适用,《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13(2) 条规定:“平民居民本身以及个别平民不得成为攻击对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习惯法研究以以下措辞表达了这一原则:“冲突各方必须始终区分平民和战斗员。攻击只能针对战斗员。攻击不得针对平民。”该规则以客观术语表达,不涉及特定行为者的意图或心理状态。这些来源中使用的任何术语的定义中都不带有主观因素(例如,《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0(1)条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研究报告第 5 条中“平民”的定义是客观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关于“平民”定义的争议与这一点无关)。
也没有迹象表明意图包含主观因素
相反,这些条款的上下文证实了其客观内容。例如,《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85(3) 条将“以平民人口或个别平民为攻击对象”列为严重违反行为(即那些除了国家责任外还涉及个人责任的违法行为),但仅限于“故意实施”。刑法标准中明确纳入了犯罪意图要求,作为区分基本原则(人道主义法标准)的补充,证实了该基本原则本身缺乏这样的要求。
一些实践表明,区分原则中必须包含意图要求。最明确的是,以色列参考《第一附加议定书》标准提出,“指挥官的意图对于审查武装冲突期间的区分原则至关重要”(外交部,《加沙行动》,2008 年 12 月 27 日至 2009 年 1 月 18 日:事实和法律方面》,第 110 段)。但如上所述,这并不准确:虽然意图对于个人刑事责任至关重要,但违反人道主义法标准则涉及国家责任,因此不包含任何此类主观门槛。还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有限的实践无法达到通过后续实践修改法律所需的门槛。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其他相关规则确实可能包含某些主观因素
例如,比例原则禁止“可能造成平民生命附带损失、平民伤害、平民物 纳米比亚电报号码 体损坏,或三者兼有,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过于严重”的攻击(《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1(5)(b) 条)。“可能”和“预期的军事利益”的提法表明了攻击时所掌握的信息的相关性。然而,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提出真正的主观测试。例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分庭在检察官诉加利奇案 (第 58 段)中认为这设定了合理人格测试。
“严重违法”
国家责任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均缺乏普遍适用的主观标准(如前所述,至少某些规则,如区分原则,是纯粹客观的),因此,这种普遍标准 向客户发送有针对性且高度相关的外 只能来自标准 2(c) 中对人道主义法“严重违反”的提及。英国政府在其论点大纲中也主张这一立场: “‘严重违反’一词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具有特定含义,与‘战争罪’和‘严重违反’同义”(第 38 段)。此外,如前所述,高等法院认为“严重违反”的概念包含一定的主观测试(高等法院判决第 18 段)。
这一点在之前的博客文章中已经得到很好的探讨,我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需重申,“严重违法行为”的概念虽然与“战争罪 越南推廣 ”的概念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正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其塔迪奇管辖权裁决中指出的那样,“严重违法行为”被定义为“违反保护重要价值观的规则,并且这种违反行为必须给受害者带来严重后果”(第 94 段)。这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后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其他条件之一(例如犯罪意图);因此,“严重违法行为”和“战争罪”的类别并不相同。类似地,《武器贸易条约》第 7 条中“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的概念(标准 2(c)基于此)似乎并非旨在专指战争罪(因此包含主观因素)(参见Clapham、Casey-Maslen、Giacca 和 Parker,《武器贸易条约:评论》(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6 年出版),第 7.39 至 7.49 段)。